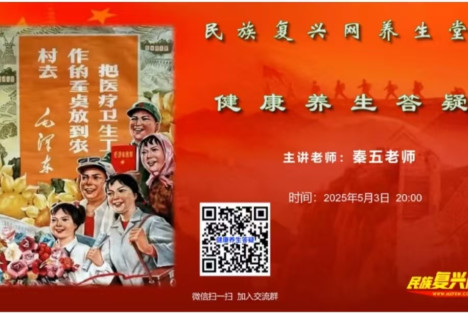你以为在看灾难片,其实是在看一场资本杀人的纪录片


《铁线虫入侵》与《流感》是韩国灾难片中的代表作,于2012年上映,由朴正祐执导,是韩国第一部以寄生虫为主题的灾难电影;《流感》则由金成洙执导,同年上映,以现实传染病危机为基础,展现大规模传染与社会崩溃的全过程。两部影片在当时均引发热议,票房表现不俗,前者更一度打破韩国科幻类影片的票房纪录。
《流感》则被视为新冠疫情前最接近现实预演的作品,在后来的疫情期间被大量重新提起。但当大众为其“预言性”感到震撼时,却往往忽略了更值得深挖的东西:这些灾难的根源,从来不只是病毒或虫子,而是更深处的体制病灶,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统治秩序本身。
《铁线虫入侵》以突如其来的寄生虫疫情为起点,构建了一场从个体到全城的生存危机。一种变异铁线虫悄然侵入首尔饮用水系统,人们在毫无察觉中感染,随之出现高烧、抽搐、自残乃至死亡的症状。最初被当作普通寄生虫处理,但迅速恶化的病例引发社会恐慌,医疗系统崩溃,政府仓促应对,最终首尔陷入瘫痪。
真正令人震惊的不是虫,而是幕后真相的揭露:首尔生物制药公司蓄意制造并投放了变种铁线虫,其目的正是引发大规模感染,以推动他们提前研发好的新药上市,从而借灾难实现股价暴涨、垄断市场。这不仅是一起人道灾难,更是一场资本精心策划的金融谋杀。
而《流感》的剧情则更具宏观性。一种新型H5N1变异病毒随着偷渡者进入韩国盆塘市,病毒以极快的速度在密集人群中传播,死亡率接近百%。影片以平民快递员和单亲母亲医生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城市在病毒入侵后的短时间内如何从运转井然走向全面失控。医院爆满、尸体堆积、政府下令封锁城市,军队进驻、隔离营设立,被感染者被强制囚禁甚至处决。
高层在国际压力下,选择对感染者展开无差别屠杀,并计划对盆塘市实行“焚城政策”,即在城市完全隔离状态下投放火弹清除所有潜在病毒源。与此同时,负责病毒控制的卫生部长竟然无权决定医疗优先级,而是要向美国驻韩顾问请示。这暴露出韩国政府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对外依附、对内专制的双重结构,而民众的命运最终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演习的附庸。
影片中的高潮出现在隔离营冲突中,成千上万的“疑似感染者”被关押、无医可治、无从逃生,面对军队的枪口,只能被动等待命令落下的那一刻。即便有医生发现幸存者体内存在抗体、可能研制疫苗,依然无法扭转“清场”决策。这不是科学选择,而是政治压制、资本逻辑下的风险控制——感染者的存在是对稳定性的威胁,是媒体恐慌的火种,是疫苗资本未成熟前的市场噪音。他们必须被“消失”。
两部电影分别以医疗犯罪与国家灾难的不同侧面描绘了一个共同的结构性真相:资本可以制造灾难、操控政府、收割生命;而制度则始终维护资本的统治。所谓“科学”“国家”“专业决策”不过是资本命令的技术外壳,它们的底色从来不是中立,而是利润。正因如此,影片虽揭露了部分真相,却又急于用个体的英雄、父爱的牺牲来为整场危机作出道德缓冲,似乎只要有几个“讲良心”的人,系统就能被拯救,恶行就能得救赎。
但现实是,群众始终不是叙事的主体。他们要么是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要么是病毒的载体和情绪的发泄口。影片没有展现真正的反抗,也没有提出任何制度层面的对策。它们将灾难归咎于“个别公司作恶”“政府操作失误”,把群众的悲惨描绘为偶然,使观众流泪之后,依旧安心地接受这个系统。这样的灾难片,看似充满批判,实则温和顺从。
灾难之下真正需要揭示的,不是“我们多么脆弱”,而是“谁在主导灾难”。不是自然异变、操作失误、技术问题,而是资本制度、利润驱动、统治逻辑。这两部电影尽管在表现力度上有一定突破,但始终止步于体制边缘,无法真正揭穿灾难之下的阶级真相。观众在视听震撼中获得情感代偿,却失去了真正的认知可能。
不是铁线虫让我们癫狂,不是病毒让我们崩溃,而是这个为了利润可以制造一切灾难的体系——它才是最大的病源。
这些电影之所以令人不安,还因为它们与现实社会的种种事件形成了惊人的呼应。2013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同样是资本为了利润,在已知问题存在的前提下继续生产、销售,导致数十万婴儿结石、畸形乃至死亡;同时,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暴露出资本逐利下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流感》上映数年后,口罩爆发,世界如同复制了影片场景:病患激增、医院爆满、民众恐慌、政府封城,甚至连“是否该屠杀疑似者以保障大局”的讨论也真实上演。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回看这些影片,才更能意识到它们虽不是“预言”,却实则反映了灾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既定运行模式:一切都可以成为牟利的工具——疫苗、口罩、呼吸机、抗体、封锁、开放……灾难成为产业链,苦难成为资本的市场机会。
在这些“灾难资本主义”逻辑中,群众始终处于被动、无力、等待“拯救”的位置。电影没有展现群众组织起来、打破信息封锁、展开阶级反抗的可能,而是将希望寄托于个别英雄、某位“良心医生”、一个哭泣的孩子——这恰恰也是意识形态的温柔陷阱。在令人窒息的末世景象中,观众无法再思考社会结构,只能寄望于人性、家庭与爱,这些本身无罪的情感,在资本主导的媒介结构中被消费、利用,最终反而成为系统稳定的支柱。
而资本,即使在被揭露之后,仍未真正被否定,它只是换了一层皮、换了一个代言人,继续在幕后运转。就连片中“揭露真相”的桥段,最终也不过是一场舆论危机管理的演练,稍纵即逝。
《铁线虫入侵》《流感》都以灾难之名,描绘了现代社会在危机中的崩溃与撕裂,揭露了资本对生死的操控与政府的依附性,但它们最终未能走向真正的批判逻辑。在观众对死亡与恐惧的情感共鸣中,现实世界的系统性压迫被遮蔽,替代的是眼泪、惊呼与道德上的自我安慰。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野中,我们应当警惕这种“批判性的驯化”过程:当灾难片成为发泄情绪的工具而非启发阶级意识的武器,它就已经被系统收编。资本的罪恶从来不是失控的副产品,而是利润最大化下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能制造病毒,更能制造“如何看待病毒”的叙述结构;不仅能创造灾难,更能让人习惯灾难、原谅灾难。
两部影片都刻意避免提出真正的问题:为什么资本有权力主导公共卫生?为什么企业可以左右政策走向?为什么灾难频繁发生却从不动摇社会根基?他们的答案,是个别企业作恶,是官僚体系失灵,是“制度执行不到位”,仿佛只要换一批“有良知”的人,问题便能解决。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伎俩:把一切系统性压迫描绘为“偶然”,把制度性犯罪缩减为“疏忽”,把群众的怒火引导向情绪发泄而非有组织的政治反抗。这种设定不仅是对现实的歪曲,更是对斗争的预防。
这两部影片表面上控诉灾难,实则保卫秩序;看似批判资本,实则为体制续命。它们通过有限度的揭露,引导观众在情绪的激荡中排毒,在虚构的“英雄”中寻慰,却始终绕过对制度根源的清算。这种“看似进步”的灾难片,恰恰是意识形态最有效的伪装方式:你越是以为自己愤怒、觉醒,其实越是被纳入了主流的控制逻辑之中。
真正的灾难,不在于铁线虫,不在于病毒,而在于那个为了利润可以制造一切灾难的社会结构本身。那不是灾难片的设定,而是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现实。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